三万英尺读余华:温暖和百感交集的人世
文 | 章程
来源 | 一点儿乌干菜(ID:NarratorZhang)


作者自绘

现实一种
八月下旬,北京飞往苏黎世,机舱幽暗,间或有调整座椅的细簌声,有乘务员的细语,有德国小孩的絮絮不止,但声响的来复,反而使一切更安静。
未几,人们尽皆睡去,微闻齁声呓语。借着微弱的光,在这十个小时的行程里,我读完了余华《兄弟》上半部。
十多天后,从苏黎世返程,读罢《兄弟》下半部。
九月下旬,南京飞往昆明,因为行程短,遮光板不必拉上,窗外是万千姿态的云,阳光斜刺里穿过窗,落在肩上,机舱通体敞亮。
我翻开余华的《现实一种》,他早年小说里对黑暗、暴力和性冷酷的叙述时常让我一怔一怵。之后,昆明归来,对余华的阅读又再次伴随了两个半小时的归途。
在三万英尺的高空上读余华,是非常微妙的阅读体验。
余华笔下的世界,如此贴近大地,可他自己倒像是离地三尺,有时他的冷峻甚至让我怀疑不止是三尺,而是三万尺。只有在此高度观人世,世间的一切才能被毫无新鲜地暴露在日光下。
作为十五岁后才到城市,而小时候在乡镇里长大的小孩,我对余华的作品有着深切的感同。
历史无形中掣肘着寻常人的命运。五十年代初,有个父辈某日在外闲坐时,被几个军人架着上了车。行至鸭绿江边,方知被拉去了战场。
没打过仗也只能硬着头皮上,他命硬,多次化险为夷,但最后被流弹炸到了脚,让人用担架抬着塞进了车子,他梦魇般的记忆开始了。
他的身下全是各种扭曲着的,咒骂着的,哀恸着的,奄奄一息的身体,秽不可见,夹着血腥味的古怪的令人作呕的味道。路途颠簸,很多身体直接被压垮致死。他在一堆身体的最上层,侥幸留得一命。
归乡后,因为负伤跛脚,组织每年只准让他领一只新鞋,他屡屡申请一双而不得。那只鞋摆着,犹如被人奚落的军功章。
我的这个父辈不识字,他并不知道现实还可以用魔幻来形容,他只是越来越难以理解周遭的世界。

作者自绘
当我邂逅到余华的作品后,我突然找到了自己身处过的或存在父辈的叙述里的现实。
余华小说里隐匿着许多能和我的经验一一对照的东西,有磊落的光明,但更多的是荒诞又可怜的生存,底层的人们为这生存耗尽了自己的聪明和气力,有迷信,有谵妄,有对生命消亡的抵抗和绝望。
《在细雨中呼喊》里,绵绵的阴雨让农民担心涝灾即将到来,「我」的祖父孙有元走遍村中的每户人家,向他们发出嗡嗡的叫喊:「把菩萨扔出去,让雨淋它,看它还下不下雨。」
孙有元甚至开始和天空较量,他对着天空吼叫,但随即失魂落魄,哀怨地叫唤道:「我的魂啊,我的魂飞走了。」
余华写道:「祖父的灵魂像小鸟一样从张开的嘴飞了出去,这对十三岁的我来说是一件离奇同时可怕的事。」
也许在成长语境里一直有着扶乩和算卦的传统,我很容易就理解了孙有元的惶恐,在远离无神论的社会底层,命运并非黑白分明,它是模糊的,动荡的,混杂的,甚至某种不敬就能遇现世报。

作者自绘
《许三观卖血记》中,许三观对三个孩子和许玉兰口头做菜的那段,只有余华才写得出吧:
「我知道你们心里最想的是什么,就是吃,你们想吃米饭,想吃用油炒出来的菜,想吃鱼啊肉啊的。看在我过生日的份上,今天我就辛苦一下,我用嘴给你们每人炒一道菜,你们就用耳朵听着吃了,你们别用嘴,用嘴连个屁都吃不到,都把耳朵竖起来,我马上就要炒菜了。想吃什么,你们自己点。」
贫贱生活里熠熠生辉的人性,大概就是这样。
我喜欢许三观这个形象,在他身上我能找到父辈的影子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他们,一生无非为了活着,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。
活着里的柴米油盐,让他们忍耐着生老病死,甚至不惜倾尽千钧气力。但谁又不为了这些呢?谁又能逃得出这柴米油盐和生老病死的命运呢?

海盐往事

作者自绘
余华生于杭州,在大约四五岁的时候,和哥哥随父母离开杭州,来到叫海盐的小县城,他们在一条弄堂底一住就是十多年。
田野,池塘,油菜花,蛙声,炊烟,水牛,蔬菜地,粪味,田埂,黝黑的身体,这些构成了他最初对生活的理解。南方的风物,气氛,节奏,方言,渗透到他生命图景中。
对幼年的他而言,土地的形象充实又令人感激。土地能接纳很多东西,甚至一个人「无论是作恶多端,还是广行善事,土地都是同样沉默地迎接了他。」
《在细雨中呼喊》中有余华在海盐时的经验。
小说里南门的两个兄弟,苏宇和苏杭,是城里来的小孩,他们的父亲是城里医院的医生,皮肤白净,嗓音温和。
这和余华的经历很相似。小说里那个能吹出卖梨花膏的笛声的少年,后来死于黄疸肝炎,在余华的成长里也确有其人。
虽然余华是弄堂里的孩子,但他更爱和农村的孩子玩,因为他们的重视让他的自尊心得到很大的满足。
《在细雨中呼喊》中,「我」与苏杭、苏宇、郑亮等的友谊,就是出于小孩子对大人的崇拜,当自尊心破裂后,「我」会迅速建立另一段友谊来掩饰落单,这是成长时期里不易察觉的骄傲与脆弱。
父亲在医院工作,所以余华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在医院里度过。他小时候不怕看到死人,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的恐惧,对手术室里提出来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习以为常。
他在死者亲属的哭声中长大,有一段时间还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为动人的歌谣。

作者自绘
王立强的死,是《在细雨中呼喊》里最触目惊心的桥段,余华把他的死安排在医院。
王立强提着手榴弹挨个搜查医院的房间,但并没有找到想杀的那个女人,他在护士值班室看到了两个血肉模糊的男孩,他们因他而无辜离世,于是他无意再去寻找那个女人。
他走出医院,在门口拉响了手榴弹,「身后的木头电线杆也被炸断了,灯火明亮的医院,顿时一片黑暗。」
这段关于毁灭的描述让人胆战心惊,似乎唯有医院,才能承载毁灭里的吃惊、害怕和怯弱。
医院是特别的社会机制的产物,在福柯的论述里医院是异托邦。
异托邦是处理危机的空间。因为病痛,我们有了身体的危机,医院对人进行治疗,让人能在社会行使正常人的权利。医院是隔离的,我们在正常社会里不愿看到的成员被放在这个特定空间里。
异托邦具有镜像作用:在自我缺席之处,看见自身。在医院这种异托邦里成长起来的余华,在此建立了自己对于病痛的敏锐,还有疏离。他从医院这个虚象空间里看到了自身,和窄若手掌又宽若大地的人间世。
在高考落榜后,余华到了镇上的卫生院,当了一名牙医。有时看到大街,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,他心里会涌上一股悲凉。
他写道:「我的青春是由成千上万张开的嘴巴构成的,我不知道是喜是忧。」转折发生在二十三岁那年,他被通知去北京改稿。
回来后,海盐的人们认为他是一个人才,不应该再在卫生院里拔牙了,于是被调到了文化馆工作。
余华自言自己和现实关系紧张,一直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。这和他在医院的童年和作为牙医的成年息息相关,这些朝夕相处的现实,带给了他丑恶和阴险,也带给了他温存和善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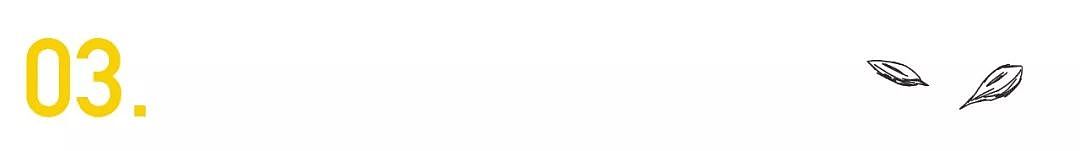
文学流亡

作者自绘
听一个作家谈论另一些作家,是一件有趣又耐人寻味的事。比如纳博科夫的《文学讲稿》,比如米兰昆德拉的《小说的艺术》。
余华也愿意谈论他在文学里的流亡。这让我们理解余华多了一条途径:从一个作家的阅读史走向这个作家。
川端康成和卡夫卡是对余华影响深远的作家,他如是写道:「川端康成是文学里无限柔软的象征,卡夫卡是文学里极端锋利的象征;川端康成叙述中的凝视缩短了心灵抵达事物的距离,卡夫卡叙述中的切割扩大了这样的距离;川端康成是肉体的迷宫,卡夫卡是内心的地狱;川端康成如同盛开的罂粟花使人昏昏欲睡,卡夫卡就像是流进血管里的海洛因令人亢奋和痴呆。」
川端康成和卡夫卡这两种绝然不同的语言,流向一个写作者的内心,让他开始用内心的波动来触摸事物。除了小说家真诚又狡猾的那面外,余华还有柔软缓和的另一面,所以他在《许三观卖血记》里没有把生活写得彻底绝望。
伟大的作家的内心没有边界,「没有生死之隔,也没有美丑和善恶之分,一切事物都以平等的方式相处。」
我阅读卡夫卡要早于阅读余华。「寻找」是卡夫卡小说中的母题,他的三部长篇小说《审判》、《美国》和《城堡》的基本情节均是主人公的「寻找」之路。余华的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也是关于「寻找」的寓言。小说中父亲对「我」说:「你已经十八岁了,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。」
可是「我」在与难以理喻的世界较量后遍体鳞伤。小说里的「寻找」,既属于生命个体,也属于一代人。它的结尾是开放的,结局的不确定,让「寻找」也具有了荒诞感。
卡夫卡的荒诞是二十世纪的精神特征,他本身就是极端内敛的性格,这让他能敏锐地感知到现代人的处境。余华也有这种禀赋。
余华的荒诞,是当代的生存图景。《兄弟》的下半部,有人说不好,但我觉得没有其它作品比它更能描述这个时代的乱象:伦理颠覆,浮躁纵欲,革囊众秽。
当代人说当代事并不容易,每个人都在做着判断,都在信息的泥淖里挣扎。时代有足够多可以被创作的素材,可更深刻的感知总是缺席。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,我们身处在越来越轻的时代。
卡夫卡对暴力的叙述异常冷静,他在《在流放地》里细致地描写了一台杀人机器,它由三个部分组成:绘图员,耙子和床。床头还有一块毡子,塞在犯人的嘴中,阻止他喊叫。耙子在犯人身体上刻下罪行,直至他死亡。小说的结尾,军官用这台机器处死了自己。
余华对于暴力的迷恋在早期的小说里就见端倪,譬如《一九八六年》描写了一个消失的中学历史教师重返家乡后,对自己的身体处以极刑,「墨、劓、剕、宫、大辟」这五刑光看文字就足够震慑了,可余华不满足于此,他以文学的语言延长了整个暴力过程,仿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《罪与罚》中描写拉斯柯尔尼拿斧子砍向放高利贷的老太婆。
余华坦言:「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,它的力量源自人内心的渴望,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。即便是南方的斗蟋蟀,也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暴力是如何深入人心。」

作者自绘
除了卡夫卡,博尔赫斯也巨大地改变了余华。博尔赫斯喜欢在故事的叙述里分岔出无数可能,他乐此不疲地创造着迷宫。现实在他的笔下扑朔迷离,神秘又虚幻。
余华的《世事如烟》就有这样的特质,犹如看大卫林奇的电影。七个家庭十多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,趔趔趄趄,不知去向。梦境和事实被混淆,怪诞诡谲。
《在细雨中呼喊》时常出现离奇的描述:「(国庆)经常向我和刘小青讲起他的母亲,怎样在黎明前无声地走过来和他说上几句话后又无声地离去。当我们询问究竟说些什么时,他却神态庄重地告诉我们这应当是保密的。
有一次他母亲忘了回去的时间,公鸡的啼叫使她大惊失色,急忙中她没有从门口出去,而是破窗而出像鸟一样飞走了。我曾悄悄问过刘小青:「她会不会摔死?」刘小青回答:「她已经死了,就不会怕摔死。」我听后恍然大悟。」
和博尔赫斯一样,在余华的叙述里,生死的界限不分明,他是鲁尔福或马尔克斯式的作家,死者在他们的叙述中复活,内心的迷信、阴暗和恐惧在小说里得以解放。

死亡叙述

作者自绘
余华对死亡的叙述特别冷静克制。这和他从精神狂热、压抑本能的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经历不无关系,死亡在那个年代稀松平常。
他曾因为对正在被批斗的父亲说了一句:「这火是我哥哥放的。」而让父亲历尽磨难,在批斗会上不知道痛哭流涕了多少次,「他像祥林嫂似的不断表白自己,希望别人能够相信他,我们放的那把火不是他指使的。」
他在《兄弟》里将这个记忆进一步扩大。因为李光头对父亲宋凡平说了一句:「明明是「地主」两个字,你说是「地」上的毛「主」席。」宋凡平被红袖章揍得死去活来,他们吼叫着,几只脚对准地上的宋凡平又是踩又是蹬,「要宋凡平老实交代他是怎样恶毒攻击伟大的领袖、伟大的导师、伟大的统帅、伟大的舵手——毛主席。」
宋凡平之死是书中最不忍卒读的章节:「从不屈服的宋凡平这时候太想活下去了,他用尽了力气跪了起来,他吐着满嘴的鲜血,右手捧着呼呼流血的腹部,流着眼泪求他们别再打他了,他的眼泪里都是鲜血。……那些脚在继续蹬过来踩过来踢过来,还有两根折断后像刺刀一样锋利的木棍捅进了他的身体,捅进去以后又拔了出来,宋凡平身体像是漏了似的到处喷出了鲜血。」刘妈目睹了这一切,她看着他们瘸着走去,自语道:「人怎么会这样狠毒啊!」
在一个反智的年代,生命如草芥,如蝼蚁。人们挟荒唐报私仇,随便拿一个罪名,写到大字报上,再贴出去,用不着自己动手了,别人就会把他往死里整。
《活着》中的福贵经历了那个年代,死亡夺走了他身边所有亲人。话剧《活着》里,黄渤饰演福贵,苦根死去后,舞台的背景被灯光打成暗红色。
福贵跪倒在地,以头抢地,悲痛欲绝。他双手握紧瓶子,向下猛力击打。水从瓶中溅出,在暗红的灯光下映照得如血一般。
我第一次感受到戏剧的力量:反复的击打,渐至把人内心的防备击垮,渐至悲悯与善良流露开来,渐至让人理解死亡,渐至人们能肃穆地谈论生命。
余华看待死亡的态度,无非来自他对生命的尊重。我个人偏爱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。
许三观在自己生日那天,看着三个孩子把放了糖的玉米粥喝得稀里哗啦响,心想:「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完?小崽子苦得都忘记什么是甜,吃了甜的都想不起来这就是糖。」
温暖又百感交集的人世,永远不乏凌厉的苦难,我们若还能记得其中的甜味,这世界总归还有希望。

作者自绘
* 作者简介:章程,南大建筑学研究生。野生建筑师,青年写作者。简洁有趣,知行合一。盖过几栋房子,写过几篇文章,得过数次国际建筑设计大奖。
个人微信公众号:一点儿乌干菜(ID:NarratorZhang),豆瓣账号:夜第七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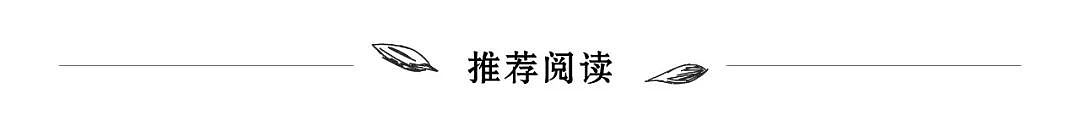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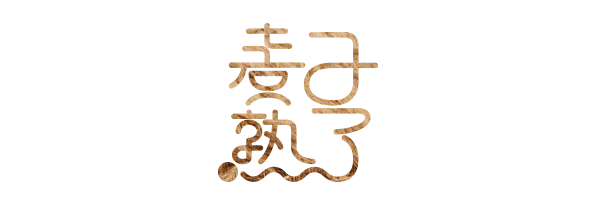





 +61
+61 +86
+86 +886
+886 +852
+852 +853
+853 +64
+64


